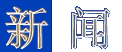天真活泼的4岁妹妹进入难民营后,每天被日本人强迫打针,一周后的一天半夜,妹妹死在我的怀里
郭来有:女,今年83岁,原为广州市芳村人,小时候的名字叫郭秋燕,逃难来到博罗县罗阳镇后,被收留她的人家改名为郭来有。
我家有6口人,妈妈在家当家庭主妇,爸爸是个“猪肉佬”,他的生意不错,我们家的生活过得很好。但在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的时候,我们家的一切都被改变了。
那年,日军对广州接连不断地轰炸,我们全家被迫逃回了南海老家。但在南海老家父母没工作,一家人生活过得非常艰难。广州沦陷后,父母亲为了生活,只好又回到了被日军占领的广州城。当时的广州满目疮痍,到处都是瓦砾。父母亲想尽办法都没找到工作,就四处讨饭吃。眼看我们4个小孩快要饿死了,这时,父母亲听到日本人到处宣传,说他们办的儿童难民营是如何如何好。父母亲为了我们几个孩子不饿死,就将我和4岁的妹妹送进了日本人办的难民营。
我和妹妹进难民营后,每天早上都被强迫打针,针是从屁股打进,用的是10厘米左右的针筒来打,这些针肯定不是治病的,因为全部人都要打针。还有我们每天吃的米饭白得很不正常,白森森令人害怕,听人说这米饭里面放了东西,才有这么白。我妹妹刚进难民营的时候,天真活泼,但住进难民营一个星期后,一天半夜就突然死在我的怀里了。我发现妹妹死了,就拼命哭喊着妹妹的名字,一直哭叫到天亮。天亮以后,日本人发现我妹妹死了,才叫人来将妹妹的尸体收走,扔进难民营的一间屋子里。难民营每天都要死很多人,有两个中国人专门收尸体,每天从早上忙到中午才能把难民营当天的尸体收完。
我看到每天都死这么多人,心里很害怕,就想办法逃走。在一天夜里,我和几个小孩趁着哨兵打瞌睡,偷偷地逃了出来。我走了一夜的田埂路,一直走到天亮,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芳村父母的身边。后来听说,没逃出难民营的孩子很多被害死了,剩余的孩子也被日本人不知带到哪里去了。
有一位博罗人来广州探亲,住在我家的隔壁,父母就向他打听博罗一带的局势怎么样,那位博罗人说还算比较平静。不久,我父亲饿死了,我母亲只好带着我和两个弟弟跟随那个博罗人来到了博罗县。我被县城一钟姓人家收留;大弟弟被博罗县罗阳浪头村一家人收留;小弟弟暂时没有找到收留人家,就跟随妈妈生活。没想到,心力交瘁的妈妈来到博罗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,妈妈死的时候才30多岁。临死前,妈妈叫小弟弟来找我,但我也没有办法养活他,就找了一钟姓人家收留了小弟弟。
虽然妈妈告诉过我大弟弟住的地方,但我一直没能找到他,后来听说大弟弟参加了革命队伍。1949年10月16日,博罗解放了,解放军进入博罗县城,我的大弟弟也跟着进城了。入城当天晚上,大弟弟到处打听,好不容易才找到我家,我们两姐弟分开多年,终于在博罗解放这一天团聚了。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来了,我的父母和小妹妹不会死去,我和两个弟弟就不会分开。是日本鬼子把我的家害成这样的,我恨死了日本鬼子!
我原是香港人,那天,从电影院出来,我就被日本兵抓走,投进了香港难民营,在难民营里人人每天都被强迫打针,每天都有十几个小孩因打针死亡
何育财,男,今年75岁,1931年出生在香港,排行老大,下面有两个妹妹,现为博罗县柏塘镇低坡村委会人。
1941年,日军进攻香港。一天,我和几个同伴钻进一家电影院看电影,没想到出来的时候,街上戒严,我被日本人抓走,投进了难民营。我呆的这个难民营是专门收留小孩的,一个木棚打着3排地铺,睡着几十个小孩,大家挤得密密麻麻的。难民营里很多小孩都在哭着找自己的父母。难民营每天提供两顿很稀的碎米粥,每天早上每人打完针后才能吃粥。每天都有十几个小孩因打针死亡,我看了非常害怕,我怕我会死在难民营里,日夜都在哭,想出去寻找家人。
难民营周围都用铁丝网围住,门口有人放哨,不准任何人外出。晚上12点后就在铁丝网上通电,天亮才断电,防止难民营里面的人逃跑。有一位被日本人抓来照顾我们的阿婆,她看见我哭得那么可怜,就教我在晚上铁丝网没通电之前爬过铁丝网,我按她的方法在一个晚上爬过铁丝网,逃了出来。
逃出难民营后,一次在街上讨饭时,又被日本兵抓住送上了军舰,军舰在海上行走了一段时间后把我们丢到深圳海岸边就不管了。上岸讨饭期间,有位在龙岗墟镇上卖鸡的博罗县柏塘人,见我长得还算机灵,就把我叫了过去,说要带我去找碗饭吃。我听到有人能为我寻找一条生路,就二话不说,跟这个人走了。我跟着这个柏塘人走小路,翻大山,不知走了多久,才走到博罗县的平安镇,在平安镇一户人家呆了一个多月后,才在柏塘镇低坡村找到收留我的人……
经过这么多年了,我一直很想寻找回在香港走散的妹妹。解放后,我曾经多次写信给香港红十字会要求帮忙寻找妹妹,但都因线索太少,香港红十字会无法找到我妹妹和家人。现在只有我母亲留下的一块日本明治年代的硬币,被我缠在腰间保留下来,使我时时不会忘记60多年前那悲惨的一幕。
小脚的母亲带着6岁的孩子,离开广州翻山越岭辗转来到柏塘鹅寨,嫁给了当地一名单身农民,但继父没法养活我们母子俩,只好再为母亲寻找收留的人家,母子俩活活被拆散了
张焕带,男,今年71岁,原为广州市人,现为博罗县柏塘镇鹅寨村人。
我是广州人,其实我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,也不知道我真正的年龄,现在我姓张是随我养父姓。我从小亲生父亲就去世了。日本兵侵占广州时,百姓举家外逃,偌大的广州城走得空荡荡的,我母亲也带着我逃出了广州。出了广州城,我们母子俩不知该往何处走,有一位在广州做生意的博罗县横河人,说可以为我们母子寻找一条生路,母亲就带着我跟他走。为了躲避日本人,我们都是挑小路走,一路上我们过得很凄惨,边走边讨饭吃,我脚都走起了泡。我母亲是个小脚女人,走远路更是辛苦。但为了能生存下去,母亲也只好咬紧牙关继续走,脚磨破了,鲜血直流。
我们经过龙门麻榨,博罗平安、横河,翻山越岭终于来到柏塘鹅寨村。到了鹅寨后,经人介绍我母亲嫁给了当地一个姓张的单身农民。原本以为经过这么艰辛的逃难,现在的生活可以安定一下了,没想到,更悲惨的事还在后面等着我。母亲是个小脚女人,原本在广州根本就没做过农活,来到鹅寨后,没办法下田干活,我和母亲只能靠继父养活。我的继父只是一个给别人打工的农民,他挣钱很少,没办法养活我和母亲两个人。别人看见我家的情况后,就给我继父出主意:留下我来做儿子,把母亲给别人带走另寻生路。
我和母亲是农历正月来到鹅寨的,还没住上一个月,我和母亲就被迫分开。母亲不肯离开我,但被人硬拖着走了,母亲边走边哭喊,我也拼命哭,挣扎着要跟母亲走,但被大人抱着不准跟母亲走。就这样,我和母亲分开了,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。母亲一直杳无音信,我估计母亲很早就去世了……
母亲走后,继父去帮人打工,每天挣回一点米。白天继父不在家,我只好自己煮饭吃,我年纪太小不会煮饭,经常饭做成粥,或者把饭煮糊了,饭里放点盐就凑合着吃,当时我仅五六岁,真是凄凉。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,我怎么会和母亲分离?小小年纪就要逃难、独立生活呢?日本鬼子真是可恨! 本报记者朱如丹 特约通讯员徐穗辉
|